
<sup id="ecicy"></sup> 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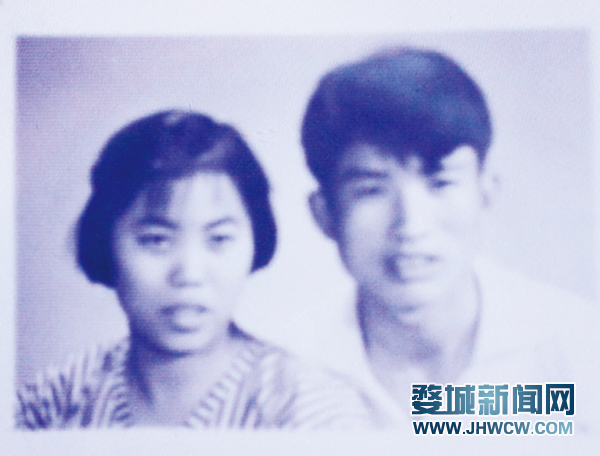

17歲那年,她當上了老師
見到朱妙貞時,她已是68歲的老人,頭發花白,面色紅潤,看樣子身體不錯。說起曾經的艱苦歲月,老人的記憶一下子就打開了……
1946年,朱妙貞出生于金華城內,她是家中獨女,自小就受到了父母的疼愛。朱妙貞幼時就喜好學習,學習成績一直是班中的佼佼者。初中畢業前夕,班主任金老師帶了班中7位尖子生去報考衢州一中,只有朱妙貞一人順利考上。可惜家中傳來噩耗,朱妙貞的父親患了重病,為了省錢醫治父親,她只好放棄了高中的學業。
朱妙貞的母親當時在居委會工作,經常與八詠樓附近的一所小學(現啟明小學地址)的校長接觸,該校長聽說初中畢業的朱妙貞閑置在家,還未找到工作,就多次鼓動她的母親讓她來學校當老師,因為就當時受教育程度而言,接受過初中教育的朱妙貞已經算是“高材生”了,學校很缺少這樣的人才。
想著可以一邊教書,一邊繼續學習,考慮許久后,朱妙貞答應了這份差事。17歲那年,稚氣未脫的她第一次踏上講臺,過起了執教學子的生活。“全校6個年級,只有9個老師,師源緊缺,我要教一到三年級的體育,四年級的語文,還有五、六年級的自然、地理”,朱妙貞說,雖然自己是全校年紀最小的老師,但教學任務依然繁重。但即便如此,她依然時刻謹記著母親的教誨,“母親對我教育很好,她說我少不經事,更應該跟前輩們虛心學習,因此,我每天都是最早到學校開門,打掃辦公室、擦桌、拖地,晚上放學,又是最后一個離開學校,關好校門才走”。
因為認真積極的工作態度,執教半年后,資歷尚淺的朱妙貞就破天荒地拿到了學校的“教育積極分子”稱號,校長還有意栽培她做學校的大隊輔導員。
上山下鄉運動,18歲的她因母親而加入了知青隊伍
1964年,上山下鄉運動在全國如火如荼地展開,也就在這一年,朱妙貞的命運改變了。
“當時,金華也掀起了知識青年支援農村,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熱潮,但我是獨生子女,原本并不需要下放到鄉下,可母親是居委會干部,為了做好干部帶頭作用,她首先推薦我下鄉”。得知這一消息后,朱妙貞并沒有覺得特別委屈,“別人都說三年以后就能回城,我想著鍛煉鍛煉也好,怕什么。如今回憶起來,才覺得那時自己有多年輕氣盛,天不怕地不怕。”朱妙貞說。
臨別的氣氛總是特別傷感,知道“朱老師”要走,學生們直抹眼淚,校長也是千萬個不舍得,覺得一個知識分子跑去種田,實在屈才。但朱妙貞卻云淡風輕,帶著簡單的鋪蓋和一個箱子就一頭扎進了金華第一批下鄉隊伍。
當時,金華首批下鄉知青共有18名,年齡均是十八九歲,最小的是16歲,這18名青年被分配至湖鎮下庫公社客路大隊(當時隸屬于金華縣),離金華三四十多公里。也許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關系,出發的那一天,大家聚集在人民廣場,雄赳赳氣昂昂地坐上戴著紅花和紅標語的汽車,那感覺,不像是去農村“吃苦”,更像是一群青年外出游玩。直到汽車開了一個半小時,眼前景色從城市的繁華變為農村貧瘠的泥巴屋,一群人才意識到“接下來的日子不好過了”。
“那天我們先到公社,后又被分到8個生產隊,由大隊的人領著來到不同的自然村,我和另外兩位知青被分配到了一起”。下鄉的知青每人有130元安家落戶費,這筆錢看著金額不菲,但這錢包括造房、買家具、制備農具等一切生活用品。初來乍到之時,朱妙貞和另外兩位知青都不敢擅自花費,沒地方落腳的他們,先是住進了大隊里的會計辦公室,后又借住到了農民家中,最后三人合力才造好了各自的茅草屋,在小村里安定下來。
繁重勞作的日子里,她體會著苦中有樂的生活
剛去生產隊報到的時候,正值9月份的農忙時節,農民們都忙著割稻子,朱妙貞也沒閑著。每天早上7點,她就起床下地干活,一直到太陽下山才回家。翌日,又重復同樣的勞作。
朱妙貞說,這還虧得以前在城市里勞動的經驗,不然身體可真吃不消。“以前校園里也可以種菜。農忙時,學校還會抽出一個星期的時間帶我們去農村剝玉米、割稻子,有時我們也會去工廠車間打工,勤工儉學。”但農村到底不比城市,日積月累下來,朱妙貞也是瘦了一大圈。
不過,在繁重的勞動中,她卻總能找到自得其樂之處。記得第一年11月份,正值冬日,朱妙貞與七八人相約一同去山中砍柴,當時農村實行封山禁林政策,山林靠外的一圈都不讓人砍伐。一群人只好凌晨四點摸黑起床,打算徒步30公里進深山,因為路途遙遠,大家閑來無聊,就一路走一路唱,合著《山丹丹花開紅艷艷》的歌聲,這群背著扁擔和砍柴刀的青年,嬉笑打鬧著,將這份“苦差事”活生生變成了游山玩水的“樂事”,渾然不覺間,竟走完了陡峭的山路。
“進山以后,雖然不覺很累,但作為女孩子,我的體力還是差了一點,男孩忙著砍柴,我砍不動,就撿地上的干樹枝,拾掇了20斤”。下山之時,已是下午3點多,朱妙貞一行看到對面山頭也有幾個人頭在攢動,就扯開嗓子在大山的回聲中互相聊起天來,這一來一回,聊天的樂趣令身上的疲乏又減了大半。
挑挑歇歇,晚上8點,大伙才回到了村子,村中一戶貧下中農見這群“孩子”忙了一天,連口飯都沒顧得上吃,主動招呼他們來家中做客,“他家連一片菜葉也沒有,只好把地瓜炒咸了,當菜給我們吃”,朱妙貞說,那頓飯雖然簡陋,但農民朋友的那份情誼,令她一輩子都不會忘記。
下鄉半年后,由于心疼朱妙貞去農村吃苦,身患重病的父親郁結心頭,早早離世。之后,母親隨慰問團來農村看望女兒,見朱妙貞生活條件那么艱苦,便辭去了城里的工作,留下來陪伴朱妙貞。母女倆就此在農村定居下來。
7年下鄉生活,她與農民締結了深厚的感情
下鄉的第二年,因為踏實肯干的品質,朱妙貞再次遇到了人生的轉機。
一日,她與農民下地掰牛糞。“以前種地沒化肥,牛糞就是最好的肥料,那時,牛糞要從牛欄里拉到田里,再由人工分開,當時也沒手套,大家都是徒手就掰,臭不可聞”。犁好的一行地,每人分工各一行,將掰好的牛糞撒在地里,農民手腳快,三下五除二就掰好了,可朱妙貞是第一次,動作明顯跟不上。誰知禍不單行,牛糞撒到一半,天上竟然下起了瓢潑大雨,其他人趕緊四散避雨,一回頭,才發現朱妙貞怎么沒跟上來?原來,覺得自己工作沒完成,老實的朱妙貞不肯走,冒雨還在那掰牛糞呢!
“后來,大家一蜂窩地沖過來,幫我把剩下的牛糞都掰了,這件事,他們還在會上點名表揚我,說我原來是教書的,跑來干這種活,不嫌棄還這么認真”。朱妙貞說,因為這件事,生產隊開始注意到她,后來考慮到村中小學需要老師,就將她抽調了過來。
回到講臺后,朱妙貞又兢兢業業地工作起來。“村小的教室是一戶大戶人家房子的大廳,一共三個年級,共30多名學生,原來有一位老先生,后來因成分不好下臺了,學校就由我一個人撐著”。因為地方有限,孩子們都混在一起讀書,給一年級上課的時候,朱妙貞就讓一旁二、三年級的孩子自習,然后輪番教學,一天下來,時常累得口干舌燥,她卻依舊樂在其中。
學校放假時,為了賺工分,朱妙貞就又從講臺回到田埂,挽起褲腿干農活。“那時工分男女有別,男的干活有10分,女的只有5分,像我們這種知識青年,干活差一點的,分數又比當地的農民低,男的最多給7分,女的只給3、4分,記得一年,我一年做到頭才拿到16塊錢。”因為收入不多,朱妙貞在家養了頭豬,一日,她獨自一人去水溝拔豬草喂豬,因為不熟悉水溝的情況,上來時,才發現兩條腿都叮滿了螞蝗,“數起來有幾十條,把我嚇得夠嗆,那時也不知哪來的勇氣,一邊用手搓一邊用腳蹬,把螞蝗都揪了下來”。
1971年,湖鎮下庫公社要抽調首批知識青年回城,公社黨委書記在挑選名單時,聽說了朱妙貞這些年來的工作,很是肯定,將她和她同為知青的丈夫都抽調回到了金華。那年3月17日,結束了近8年的下鄉生活,朱妙貞已從18歲的大姑娘變成了25歲的村婦,將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華都撒在了農村,這連頭帶尾的8年,也讓她和農民締結了深厚的感情。
“走的那天,他們也哭,我也哭。當年進村,空著雙手去,回來那年,農民幫我們推著2個獨輪車的家當,從湖鎮下庫公社一直拉到了金華,三四十公里路,來回幾個小時,這感情,能不深厚嗎?”朱妙貞說。
如今,69歲的朱妙貞已從單位退休,但這么多年過去,她依舊與當時下鄉時結識的農民們保持著密切的聯系,每年還會回村里看看老朋友,“有些是教過的學生,有些是一起干活的同齡人,有些是照顧過我的老人,但很多都已經去世。常有人覺得,知青下鄉很苦、很累、很委屈,但我現在回想起來,這樣苦中有樂的生活彌足珍貴,因為以前大家那種互相幫助,善良淳樸的情誼,是現在體會不到的……”

看婺城新聞,關注婺城新聞網微信
<sup id="ecicy"></sup>